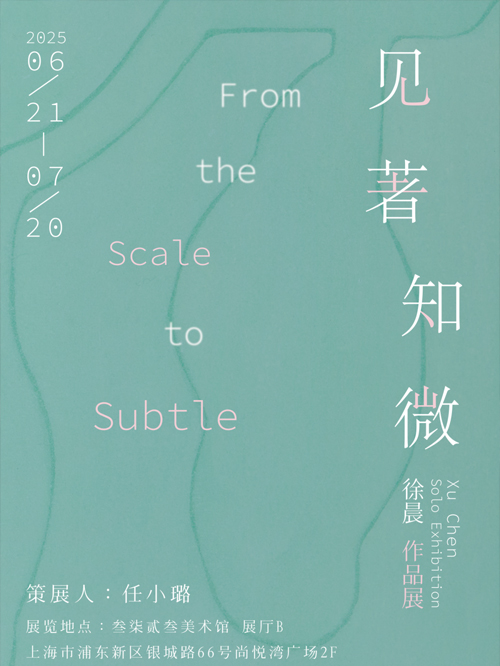01
展览始于一段旧事。
1967年,即将而立之年的曾孝濂,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停止工作一年后,接到了一份特殊的任务:继续作为特别工作小组的植物画师,参加“523”研究考察特别行动,担任植物绘图工作。彼时,美国正入侵越南,恶性疟疾在云南不远处的战区流行。这个由国家牵头成立的“523”攻关工作队的任务,便是在云南边境线的广袤雨林中寻找治疗疟疾的中草药。
此后五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曾孝濂都在与越南、老挝、缅甸边境林区中度过。他需要将工作队前期考察、分类、实验后的植物名单,进行实地的写生。之后,交付画稿,最终图稿文字编印成册,交给部队试用验证。同时下达的还有编绘《热区野草图谱》和《热区骡马代用饲料图谱》两项任务,它和《疟疾防治中草药选》的故事,成为这个展览的开篇。

“523”任务中参与绘图的《热区野草图谱》、《热区骡马代用饲料图谱》和《疟疾防治中草药选》封面
“523”任务,成为曾孝濂真正进入和体验大自然的初始。然而,它对曾孝濂有着更为深层意义的情感,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旧事”。或许,正是这次“偶然”的任务,让他在那场席卷所有人的大风大浪的时代运动中,得以从“出身”带来的灾难,身边师长的困境与迷茫中,逃脱现实,获得短暂的“宁静”与“专注”。
亦如他在50多年后的回忆录中写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我福祸皆至,两喜一忧。一喜是入选‘523’任务,没有中断绘图工作,还领略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二喜是天赐良缘,与同事张赞英终成眷属;忧的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惹火烧身,自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还殃及家人。”
57年前的那片“雨林”,成了曾孝濂的某种意义上的“避世”,也成为这个展览的缘起,这批画作出现的前提。它既是早已埋下的“种子”,又是一封迟到的“信件”。

秘境,160×119.5cm,2008
02
干季的雨林里,几乎每天都有雾。因为雨少,雾成了雨林中重要的水分补充,也因为它总是随着夜幕来临,在次日10点才逐渐散去,雾在和雨林、光线、丛生的空间中,有了某种自然浪漫主义的景象。而又因为这个“景象”在画中的迟到,它便有了某种记忆,有关“粘稠”和“恍惚”的记忆特质。
1967年,曾孝濂第一次踏入这片原始雨林中。置身雨林,就像处于濛濛细雨之中。长叶上由雾凝结的水珠顺着叶尖滴沥,树干也总是湿漉漉,吸饱了水的青苔在树干上显得格外青翠。这些观察,并非曾孝濂随队前行时匆匆得来的细微景象,工作要求他需要不断地脱队,停留在某处数个小时,进行细致地写生描绘。
幸运的是,他有机会获得与自然独处的诗意,去仔细地看待那些微小却又磅礴的关系。不幸的是,他要一个人面对危险,像是被上帝抛入一片无人之地,不能擅自离开,静等大部队将他找回。两种并峙又矛盾的情绪,让他有机会得以全身心地去感受这个世界:“远处什么也看不清,朦胧之中一片空茫,只有虚化的树影时隐时现,让原本就是秘境的雨林更加神秘莫测。而森林中最幽深的地方,密不透风,暗若黄昏。”

雨林即景,171×89cm,2019
他的目光成为“黄昏”中的光亮,那些从未被描绘过的细微植物,那些在绘画史上少有出现的另一种“自然”,也成就了几十年后这些画作中独特的“美感”。请注意这里不是“美”,而是一种“美感”,一种哲学上不可及的迷思与惊叹。也因此,这些独特的画作,虽然用水墨的材质描绘,却也奠定了它与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画,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与美学。
03
艺术的改变,不仅来自于美学自身的变迁,更多时候,它是来自于一种认识,或者说科学的认知,始终改变着艺术的形态。这样的故事从文艺复兴、印象派,到立体主义、装置和影像艺术的诞生,不胜枚举。
出身为植物博物画家的曾孝濂,有着和传统画家截然不同的“知识”和“目光”:雨林上层的树种,望天树、龙脑香凭着基因的优势,形成五六十米的树高,成为有限的阳光里第一波胜者。为了站稳脚跟,防止雨水的冲刷,乔木类的树干会长出放射性的板根。而榕树类则长出大量气生根不断地向下延伸,只要接触土壤,便膨胀为网状质感,纵横交错,以确保枝干不断地向外扩张,获得更多的土地和生存的权力。
为了争夺阳光,雨林中的植物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它们进而进化出自己独特的存活法则和生存秩序。藤本植物,由于没有直立的主干,便进化出攀缘和缠绕本领,它的趋光性像极了人的饥饿感,只要有光源方向的载体,它就能找到支点,比载体爬得更高、更远,争得一块自己的领地。这个过程,如果我们以“拟人化”的手法去描绘,有如巨蟒舒卷翻腾,气势如虹,构成热带雨林中如此壮阔的生命景观。

互生共荣,138.5×69.5cm,202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有关自然、宇宙的纪录片与电视片,总是仿佛拥有上帝视角,调转镜头,时空万里亦或万年。我们总是以人的口吻,拟人化的方式去描绘,动物、自然与宇宙的发生,发生在非洲草原上狮子与太平洋上鲸群共有的爱,丛林里与沙漠上完全不同的植物与动物部落,人们总是在其中寻找起源,寻找与我们不同的时间、空间,寻找我们可以借鉴的那些美好与衰败、爱情与道德、经验与教训。
当然,阳光不会打在每个植物的脸上,那些生活在阴影之下,却依然有着植物自身生命的美丽。众多的草本植物,既无强大的身躯,又没有攀缘、拉扯的本领,为了生存,它们进化出各种方式。树荫下的大叶植物类,例如芭蕉和海芋,它们生长出硕大的树叶,以增加自身接受弱光的面积。而另一类,没有土壤,也没有领地的植物,则学会“依附”的本领安身立命,它们的孢子往往很小,落在哪里便在哪里生长,飘落在树干上的尘土、落叶、枝桠的缝隙,成了它们居所。有趣的是,这类附生植物和寄生不同,它并不向树干索取营养,只是依附,像是曾孝濂所说的:“只住不吃”。
然而,最让曾孝濂过目不忘的,却是几种罕见的寄生植物。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没有叶绿素,没有阳光,在黑暗中也活得很自在。不过,它们的颜色与形状,却着实地迷幻,鲜红如血,或晶莹洁白,半透明,幽暗中发出瘆人的白光,又被唤作幽灵草。其中一种曾孝濂在画作中,反复描绘的植物,没有叶片,花瓣平展如盘,孤身一花,名作寄生花。
描述至此处,或许读者早已在文字中,察觉到这些植物的“现实主义”的意味。雨林的多样性,为植物、动物、微生物,提供了生存理想中的生息之地。这些生命个体交织在一起,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它们历经万亿年的磨合,命运有长有短,但它们努力地达成平衡。而在这段自然不断蜕变的历史中,人类直到很晚才出现。然而,生命之气的浩然洪流中,那些消失、努力、温情的平凡故事,亦或是壮举,都在改变着这个世界的发生。
或许说,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曾孝濂的画作,理解为艺术提供的一种认识与世界观,它经由1967年的那段旧事,植物与动物的世界开始。作为一种经验,也作为一种治愈,来面对今天我们所处的动荡不安世界,全球化共生体系的衰退,困扰已久的边界纷争,极端的战争冲突,意识形态的对立,宏大世界的席卷与渺小生命的漂泊种种。
只是,自然世界早已提供了答案,亦如中国古人所言的“道法自然”,现代译为“向雨林学习”。
04
如今,这段往事已过去57年之久,描绘自然中的生态,既是曾孝濂多年的梦想,又是他创作的主题和中心。也正是因为这个“主题”,从传统的艺术表达,转向对生态、秩序和自然启示的探寻,尤其植物、生态、自然等话题,在全球双年展和美术馆中的涌现,这批作品冥冥之中具有了某种“当代”的意味。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份迟到的礼物,某种意义上,这个展览又是送给云南的,“这里特殊的地理环境,垂直的气候类型,孕育了云南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使得云南各类群生物物种接近或超过全国的一半,并以‘动物王国’‘植物王国’‘物种基因库’名冠天下。如果研究生物学不谈到云南,是绝对不可能的。”
它亦属于一段漫长而又独特的历史,作家聂荣庆写道:“1436年,云南人兰茂写出了《滇南本草》成为中国最早的植物志之一。1638年夏,徐霞客第一次进入云南,之后三次游历云南山水叹为奇观,留下滇游日记26篇,有一篇记述云南山茶和杜鹃花形态的美文《滇中花木记》,‘映日烧林’的马樱花、大如鸡卵的牡丹花,就是这位380多年前的明代旅行家留给云南植物花卉的传神写照。
200年后,曾任云南巡抚吴其睿,编撰的《植物名实图考》,成为我国19世纪重要的植物学著作,详细记载了每一种植物的形色、性味、产地、用途等,附有精美绘图。它在植物学史上的地位,早已为古今中外学者所公认。
历史亦由外来者开启,它勾勒出另一番影响世界格局的全球史。1882年6月,法国传教士赖神甫到达云南昆明,一个月以后前往大理、丽江一带传教并收集植物标本。1883-1896年的13年间,赖神甫为巴黎自然博物馆送去了来自云南横断山脉的大约20万份植物标本及数百种云南种子。法国拥有了研究云南动植物资源的第一手资料。
之后,‘植物猎人’的足迹,遍布云南。1922年5月,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来到云南丽江,此后27年时间里,他先后6次进入云南,足迹遍布大理、丽江、迪庆、怒江等地。洛克对云南的人文地理、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当然作为一个植物学家,他更为热爱云南生物资源,并留下了极其重要的研究成果。”
或者说,在曾孝濂这条独特的轨迹背后,我们既能看到一段始于15世纪的中国中草药、自然游历在云南埋下的种子,始于16世纪的西方殖民史烙下的阴影,亦能从中窥视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和新科学运动中现代性的兴起,民族意识的自觉。直到50年代,开始建立自己的植物志,一个初生的现代国家和民族国家试图在植物学中建立的“光荣”与“梦想”。
当然,我们亦可以把这个轨迹缩小,这份“雨林中的来信”,途径了哪里?60年代那场运动,让一个年轻人在遥远的雨林里获得了弥足珍贵的自由,在那个个人犹如沙粒的年代,“不可思议”地开始了生命与自然的思考;70年代,作为中国第三代植物博物画家,开始尝试在客观之外,建立中国自己的风格;80年代,曾孝濂带领一批年轻人,将植物博物画带向艺术的思考,以寻找历史的突破;直到1997年,曾孝濂退休,才从集体工作中抽身而出,开始画自己的创作,开始回归个人的生活。这条轨迹亦可以简化为1967年的雨林来信,只简略地写下:从集体到个人的故事。

静谧,124×92cm,2010
05
和1967年“写信”的年轻人相比,收到时,曾孝濂已经老了,他必须格外地吝惜时间。
遗憾的是,这份埋藏了多年的愿望,直到多年后才得以实现。在这期间,他既沿袭着“植物博物画”给予的严谨、客观和科学的经验,又要不断学习各种传统的艺术技法,不断地尝试将主观与客观进行结合。幸运的是,早在1967年,他便建立了人生的信念 ,有些人一生做很多事,有些人一生在等一件事,怀揣着“梦想”,便是过程的幸福。
一种坚定不移的目标感,但这样说过于隆重,毕竟这里是昆明,那些懒散、慢半拍的生活,不允许过于宏大。这里有自然主义,这里的海拔有些高,你不能太急,你得一笔一笔的填,不然就会气喘吁吁。也因为只有两季,日月星辰有着独有的诗意,食物充沛,人们有时间去回馈太阳、雨水、泥土,“回馈”便是幸福。
或许,只是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曾孝濂的作品为什么将我们打动。他的生活有不幸,但一生只做一事,让我们这些困于更多、更好、更坏选择的人,在欲望中盘桓与时刻计算的人,看到围城之外的人生。他又幸运地画上了植物、动物与雨林,那些生命如此绽放之物,只会给你惊喜,不会辜负你,更不会给你复杂的人际。在这个意义上,植物比“人”好。
当然,尤其在疫情时,当你困于某时某地,数千公里外的森林依然花开花落,万物有声。哪怕是窗外,落下的一片树叶,墙角里枯死的植物,生出的一只绿芽,它和你无关,但又仿佛不离不弃,这便是生命给我们的含义。

毛脚龙竹,117.5×89.5cm,2019
直到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曾孝濂的植物画,让我倍感治愈。那些“植物”那么不现实,画中的“时光”又那么的专注,心中仿佛别无他物。时间在画间细密的笔画中不知不觉地流淌,从清晨正午到黄昏,从叶上的露水到沉默的湖面,在树梢上一寸光阴、一寸生长中发生。我知道,这是我过不了的人生。
但哪怕你想想,哪怕只有几天,你听听鸟鸣、看看光在叶子与树梢间折射的形状,哪怕你也不知道光的方向。你也明明知道,雨林里满是危险,你若平等的赤身裸体,也不过和其他植物一样,经历新生与死亡。但在雨林里,在自然轮回里,你不会渴望不朽,也不会渴望伟大,你可以接受躲在树根下的某个树洞里,或是住在大叶植物下生活,如此的安心。
但若是幸运,你便拿起画笔,使用时间,画下植物上长满的细小果实。这个行为,我们称之为“意义”。


曾孝濂,1939年生于云南,1958年就职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现生活于云南昆明。从1959年起,作为编纂工作的其中一员参与《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工作,从此之后,曾孝濂以艺术家的表达、以科学家的眼光观察,一笔一划认真描绘。1990年代起,曾孝濂在为科学研究的同时,又一直坚持个人艺术风格的思考和创作,每天犹如修行一般的绘画,早已超越了所谓工作与艺术的边界,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创作并发表了2000余幅动植物图谱,设计了10余套邮票。曾孝濂的艺术显现了一种独特的连接作用,这种科学与艺术连接,既有艺术学的意义,也有社会学的意义。让我们思考今天的艺术如何在跨学科的复合范畴中继续发展。


崔灿灿,策展人、写作者。其策展的主要展览和活动自2012年起至今已有近200场,群展包括“夜走黑桥”、“乡村洗剪吹”、“不在图像中行动”、“六环比五环多一环”、“不合作方式2”、“十夜”、2013-2018年过年特别项目、“策展课”、“九层塔”、“断裂的一代”、“小城之春”、“游牧在南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