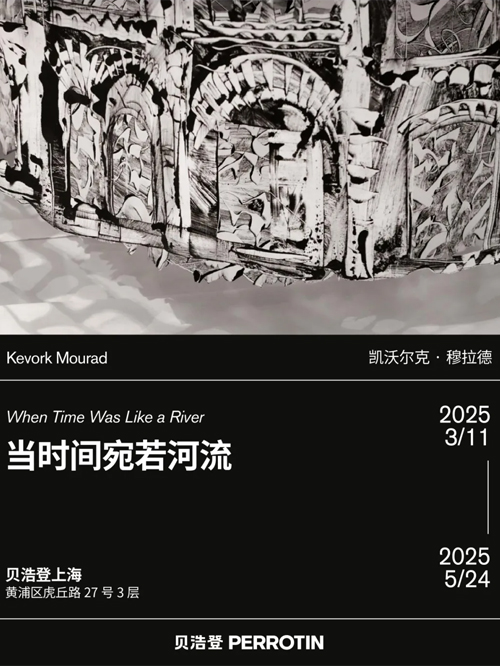冬在土中,身体活如老蚕,有毛能动。至夏则毛出土上,连身俱化为草。 若不取,至冬则复化为虫。
——吴仪洛,清 · 乾隆,《本草从新》(1757),〈冬虫夏草〉
3 月 23 日,在北纬 11° 24',东经 143° 16' 处探测到底部,测得最深的深度为 4475 寻(约 8160 米),这是整个航程中探测的最深结果。来自该深度的样本是一种深色的火山沙,含有锰矿。由于巨大的压力(约每平方英寸五吨),大多数温度计都被压坏了。不过有一支通过了考验,温度显示为 33.9 度(1.6° C),表面温度是 80 度(26.7° C)。
——Spry W.J.J,,《挑战者号的巡航》(1880)
1.
冬虫夏草最早见于8世纪的唐代,曾经人类认为这是一个物种的两个生命形态,如今已然确定的真菌寄生于昆虫,是要到了19世纪才会出现的植物学视角。科学之所以能重新定义世界,主要是人类发明了新的观看标准, 创造出一种新的视觉经验。这种新的视觉经验和过去的最大差别在于它能说服人类接受违反直觉的事实。今天人们知道,世界的奇迹在它的内部 : 菌群可以决定物种的走向,肠道里的微生物形成血清素从而影响大脑,控制人类喜怒哀乐。
2.
宣琛昊从小在冶金工厂长大,他观察显微镜切片,知道世界是从微小层级向上堆叠的结果 :半导体原料的单晶硅尺度是纳米,最终它会渲染出当代世界的外观。世界的内部决定了世界的外观,而人生活在世界的表面,人的感性也因此对表面有所偏爱。相对的,宣琛昊对这些微小而绝对的存在感兴趣,未知的模态勾起他的观看欲望,他的工作是转译世界内部的秩序和动力。
宣琛昊的绘画关于晶体的密度、膜的渗透、突触的皱褶或细胞的微弱荧光, 也关于物种在环境里的行动轨迹。世界的内部没有表情,但内部有各种结构: 宣琛昊知道结构在分子层级上是绝对的存在,它制造最基本的流动和关系。 在这里,日常世界的抒情没有效果,这里只有生命的运动。宣琛昊的语法是世界的活性。
3.
宣琛昊折叠并扩展生物族群内部的私密空间,他让它们始终具备活性。 活性意味着多边的关系,这是集群的协作而非个体的肖像。当你站在这些作品面前,请记注它们依循的是生命法理,混沌只是错觉,即兴的感官体验亦可被操控。
对宣琛昊来说,这种有关生命力的语言,可以穿破当代世界的平滑表面。

宣琛昊,1989 年出生于上海。他的作品灵感来自人工生命引擎的扩展,植物族群和细胞网络,基因组和肠道菌种,他们随时准备反抗,也随时温良的保持顺从。他试图提供这些生命力,这是关于千百年进化所达成的谱系纽带以及思维方式的通道。与其说创造,不如说是在汲取这些被造物的同时释放能量获得自由,这个过程是拒绝意义的,艺术家试图在谱系中汇总归纳这些活性症候群态。生物本身在表达上千差万别,差异性和同一性如同从冰川到犬牙交错的海岸。类似养成类游戏的建模过程,意义却在偏离范围内被赋予了力量。保罗·卡恩在论述个体和共同体生成的同一性时曾写道:“就在共同体的身份得以创造和维持的那个过程中,我们也创造和维持了我们的个人身份”。
他的作品曾展出于香格纳画廊(上海)、E.SCAPE(上海)、魔金石空间(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上海)、沪申画廊(上海)、博乐德艺术中心(北京)、余德耀美术馆(上海)、166 ARTSPACE(上海)、复兴艺术中心(上海)。